“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?”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东篱(Antonia Finnane)曾以此为题,有过引人入胜的讨论。(《近代中国》1996年第2期)作者把问题的焦点锁定在“旗袍”上,并不是想为“旗袍”打广告——要知道,在本文发表的二十年多年前,“旗袍”还多是礼宾人员的,限于正式场合;如今成为网红爆款,引领时装消费新动向,恐怕是作者撰文时所始料未及的。通过这一设问,文章想引导读者思考的是,女性如何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并在国家中影响,正如作者所言,探讨国家对女性时尚的调控,能够审视女性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。对其他社会的女性服装的研究,已经了这层重要的关联。但是,在不同社会向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中,民族服装(national costume)的命运大不相同:以印度和中国作比较,纱丽在印度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;而在中国,却似乎没有地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民族服装(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暂且不论)。八十年代的中国时尚,曾对中国旗袍与日本和服、韩国韩服、印度纱丽有相同的定位,但在作者看来,这种定位却忽视了以上服装在各自国家的地位与含义: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里,旗袍既远离市井生活,又不在高档时装之列。旗袍的这种尴尬处境,于是乎成为作者观察历史上女性和民族国家关系之议题的切入点。
旗袍的时尚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,此前社会上一度流行着夹克衫搭配裤子/裙子的两件式女装。结合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对传统价值(包括男女有别的观念)的,以及女性愈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实,安氏指出,潮流从两件式的上衣下裤/裙转变为单件式的旗袍(有男性长袍的影子),是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一种表现。这呼应了秋瑾当年的女扮男装之举:模仿男性的着装打扮,以求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。把头发剪短在女性当中成为一种风尚,也包含了同样的。

在左图的广告中,夹克衫与长及小腿的裤子或裙子的搭配,流行于五四时期;在右图的海报中,女性身上的高领修身旗袍,风靡于上世纪三十年代。采自《中国服饰的变迁》第124页。
从逾越性别鸿沟到承载女性之美,旗袍的华丽转身,其实主要发生在南京国民时期,旗袍的女性化意味被发扬到极致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旗袍被确定为正式的礼服,又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和工业社会的一道缩影。旗袍在三四十年代的独领,为其五六十年代的黯然退场埋下了伏笔。尽管八十年代旗袍曾一度重返时尚圈,然而因其穿着不便之故,又未能受到现代女性的青睐。旗袍历史的起起伏伏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,同时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,即如何在时尚蜂拥而至的背景下定义民族服装。在女性着装选择相当多元化的今天,旗袍虽不乏充实的粉丝,但不太可能再续昔日之辉煌。再看一度与旗袍平分秋色的男性长袍,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则基本上销声匿迹了。
作者由此生发出一些颇值得玩味的观点:如果说前期的旗袍和建国之后的干部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性别差异,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国人对时尚的接受,则客观上强化了性别差异——但是,在跨越性别界限的问题上,前后并无二致:当中国女性向时尚进军时,她们实际上与男性是步调一致的。作者在文末感叹,这种“默契”并不能视为性别平等的象征,只能说明女性历史仍裹挟在男性历史的线性叙事框架里,站在女性角度、展现女性特质的领域在中国社会还相对不完善。
安氏后来进一步深化了“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?”这个问题,推出专著《中国服饰的变迁:时尚、历史与民族国家》(英文版2008年),回顾中国时尚的历史。一提到时尚,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把目光转向社会,作者将这种惯性思维的由来,追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世界对亚洲的观念,这在布罗代尔的书里有更明确的表述:服装一成不变正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具体反映。诸如此类的论调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堪一击的,而造成这类的根源,很大程度上在于英语国家对非社会的物质文化的发展知之甚少——这也是本书希望填补的一个空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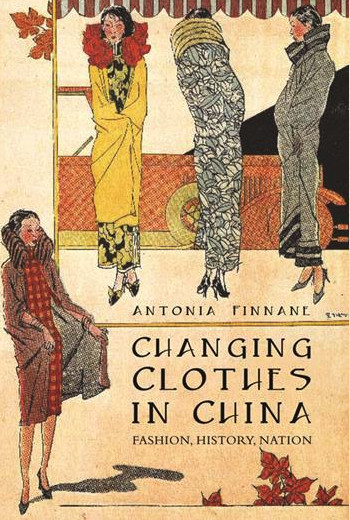
然而,此书并非一部中国服饰的资料汇编,而是夹杂着许多耐人寻味的议题,尤其是性别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。在早期来华人士留下的文字中有一种“文化相对主义(cultural relativism)”的倾向,“文化相对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文献中作为一种隐喻、一种话语出现,实际上与作为个体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关联不大”(第33-34页)。作者解释道,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,并不一定源自人对中国社会先入为主的喜欢推崇或厌恶轻视,而可能来自于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观察。这种观察既有对缠足的声讨,进而导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否定;也有对中国妇女服装的赞许,从而引出对社会和文化的反思——而对后者的研究,此前并不多见,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。安氏发现,在一些人士的笔下,中国女性的服装曾被作为正面的参照,用来质疑对女性时尚的定义,即将身体的和都置于一种满足观赏的需要上。
例如,列夫·托尔斯泰就在小说《克莱采奏鸣曲》中对女性装束中的裙撑和对肩膀、手臂乃至于的不以为然,在他看来,中国人、印度人、伊斯兰以及本国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对身体的自然呈现,相比之下要好得多。在上海发起“天足会”向缠足宣战的英国人立德夫人(Alicia Little, 1845-1926)曾写道:“对于中国人而言,外国妇女用以展现其体型的紧身服装常不得体的。我在中国的时候,尽量避免穿着形体的服装。”(《中国服饰的变迁》第38页)随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英国画家威廉·压力山大(William Alexander, 1767-1816)和美以美会驻华会督美国人柏锡福(James Bashford, 1849-1919)则认为,当时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显得既舒适,又经济,又端庄。对于服装的舒适度,身着长袍在中国旅行的英国女性伊莎贝拉·伯德(Isabella Bird, 1831-1904)是比较有发言权的。她评论道,中国各阶层女性的服装穿起来都极为舒适,没有紧身束腰之类的物件,她本人是如此习惯于中式服装以至于不想再换回欧洲的女性服装。而立德夫人在比较了服装之后,甚至生出自惭形秽的想法:“我想每个人都会觉察到我们欧洲人的服装缺乏魅力与优雅。”(《中国服饰的变迁》第40页)基于这些观察,安氏指出,从女性角度书写的历史,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线性的历史迥然有别——差异不再归结于发展时间上的先后,而是空间上的不同。


伊莎贝拉·伯德的长袍,由套在外面的无袖比甲和穿在里面的宽袖夹衣组成。最初的配图文字声称这是满洲人的传统服装,不过图片中的袖子看起来更接近于汉族夹克的款式。采自《中国服饰的变迁》第39页。
有趣的是,当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得到认可和发扬的同时,中国男性的传统服装却显得不合时宜,特别是长袍,曾受到有女性化倾向的诟病。安东篱教授在书中就提到,在时期尤其是战争阶段,社会上普遍推崇男性化的阳刚之气,在不少女性热衷于模仿男性打扮的风气之下,男性本身的气质趋于女性化(male femininity)在当时的一些人眼中,实在是令人焦虑。在大学教授沈艾娣(Henrietta Harrison)的著作《塑造国民:中国的庆典和象征,1911-1929》(英文版2000年)中,也涉及到社会的风向对提倡男性气质的影响。通过分析当时照片中的姿势,她对清末中国的传统文人和生活在的绅士进行了比较,发现前者的典型姿势是拱背曲肩的,而后者的后背和肩膀都是挺直的——这正是时期所推崇的男性形象。蒋介石早年的一张肩背挺直的照片,可以说是当时新趋势的一种反映,这种姿势不仅看起来英姿勃发,还显得为人正直有骨气,符合时人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期望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韩文彬(Robert E. Harrist Jr.)在讨论时期男装的论文(2005年)中,则专门分析了男性气质和现代性的关系。与沈氏不同,他注意到的是男性笔直的长腿所包含的阳刚之气。在传统长袍的遮盖下,中国男性的身躯,特别是腿部,被模糊化了。

左图为十九世纪末的文人,右图为在的绅士(摄于1860年)。采自《塑造国民》第81页。

然而,随着西装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流行,这种趋势有所改变。不少文字和图像资料证明,西裤似乎可以让腿部看起来更长一些,再配上大步流星的走姿势,西装衬托下的男性身躯,看起来更具有动感和活力,因此西裤也更适于鼓励竞争、进取的现代社会。不过,西装所附着的现代化标签,并没有使其顺理成章地取代传统长袍的地位,这是因为身着外国服装有可能招来非议。以溥仪为例,当时有表示,穿西装、戴墨镜的实在很难让普通的老百姓接受。

由此来看,要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语境下理解时尚的演变,不能脱离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的事件和话语;但是,诚如安东篱教授所言,中国服饰的变迁绝非国家单方面作用的结果,技术、贸易、意识形态、性别关系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,都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美感、认同和实物效用的想象和实践。在这个时尚愈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时代,从历史中汲取某种灵感、在新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,或许可以作为时尚史议题继续延伸的一种方向,同时,对于身处其中的而言,或许也可以为我们的时尚之选提供一些。
Harrist, Robert E. 2005. “Clothes Make the Man: Dress, Modernity, and Masculinity in China, ca. 1912-1937.”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,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R. Tsiang, 171-193. 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: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